中药属天然药物的范畴,自古以来,人类以动植物为食物,对中药产生了适应性,而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品对人体相对来说是生疏的异物,加之中药中含有糖类和维生素,进入体内转化为葡萄糖、葡萄糖醛酸,从而帮助解毒,有的含有蛋白质、胶质,能保护胃黏膜,缓和刺激、阻碍有毒成分吸收,且可与某些有毒成分结合成无毒物,达到消除药物自身和他药毒性及不良反应的目的,故其不良反应与西药比相对较小,疗效肯定,为中外医药界所青睐。但其固有的不良反应和不断发生的中药中毒病例,仍不得不引起医药学家们的重视。如《淮南子》:“天雄鸟喙,药之凶毒也,良医以活人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指出:“勿用相恶反者,若有毒宜制。”金元时代,我国医家综合了历代用药经验,提出了十八反、十九畏、妊娠用药禁忌等(见后“预防”部分)。公元1268年,元世祖甚至曾发令禁止乌头、附子出售入药。然而对中药毒性的了解和确定也有一个不断发展认识的过程,关于什么是毒性也曾有不同的认识。总的来说,古人对毒性认识可分为三种:一是药毒泛指药物,如《周礼》“医师掌医之政令,聚毒药以供医事”。金元时期名医张子和在《儒门事亲》中说“凡药皆有毒也”。二是药毒指药物的偏性,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说:“药以治病,因毒为能,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偏也,凡可避邪安正者,均可称为毒药。”三是指药物的毒性反应,如《淮南子》: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、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明确指出“药物有大毒,不可人口、鼻、耳、目者即杀人, 一曰钩吻, 二曰鸱(chi) , 三曰阴命, 四曰内童, 五曰鸠(zhen) 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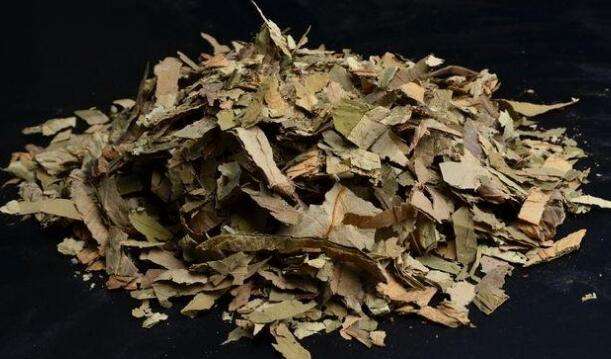
在汉代以前曾有记载:在400多种中药中有毒者占60多种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中药分成“上、中、下三品”,“下品多毒,不可久服”,如大戟、芫花、甘遂、乌头、狼毒等,后来的实践证明了,当时认为“无毒”,多服、久服不伤人的“上品”也发生了中毒死亡的病例,如人参等。而“中品”中的百合、麻黄等也被实践证明是有毒药物。传统医药学对慢性中药中毒的认识,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早在秦皇汉武时代,由于盲目追求长生不老和科学水平低下,也由于方士和士大夫阶级的误导,在社会上出现了服用金石药物延年益寿之风,这股风直到明末才基本刹住。根据著名书法家孙过庭所写《书谱》中记载,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写《黄庭经》时“怡怿虚无”即怡悦于虚无缥渺之境。这是因为《黄庭经》叙述的是与道士来往服食丹药的故事,说明王羲之也是服丹药的。去世时仅59岁。东汉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称这些药物大多“无毒”,服之可“轻身延年”“通神明不老”,因此,服食者甚众。自汉代以来,因服金石药物致死、致残者数字惊人。到了宋明之际,社会各阶层和医药学界奋起疾呼,才使这股歪风得以平息。关于动植物药的慢性中毒问题,报道甚少,真正引起医学界警觉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检索,近十七年间(1984一2000)动植物有毒中药中毒报道754篇,慢性中毒为16篇,慢性中毒占全部动植物药比例为2.12%。若加矿物药慢性中毒13篇,共见到有毒中药慢性中毒报道29篇,远较急性中毒报道为少。说明这类中毒尚未引起国内重视,或者重视程度还很不够。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中药中成药的广泛应用,在获得可喜的治疗效果的同时,也出现了毒性反应和过敏问题,每年都有不少的中毒和死亡病例的报道,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。大量实例证明,某些药物即使本草纲目和近代药典未写明有毒,在使用中也不可掉以轻心,对中药毒性的认识有一个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的过程。近年来,由于对用药剂量的忽视等原因,使一些常用的无毒药物也出现了中毒病例。
关于药品不良反应,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:“为了预防、诊断、治疗疾病或改变人体的生理功能,在正常用法、用量情况下应用药品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。”这里的药品是指合格的药品。依临床表现与药理作用的关系,药品不良反应可分为A型与B型反应两大类。A型不良反应是由于药理作用增强引起的,其反应的轻重与用药剂量有关,一般可以预测,发生率较高而死亡率较低。B型不良反应是与常规药理作用无关的异常反应,与用药剂量无关。一般难以预测,发生率较低而死亡率较高。下述的特异反应、变态反应属此型。临床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有毒性反应、1个副反应、变态反应、特异质反应、停药反应、后遗效应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(1985年版)一部就其收载的506种药材及其制品中的毒性中药分别作了“大毒”有毒”“小毒”的不同标注。
1.大毒类多指毒性大、使用较小剂量,即可迅速发生严重中毒症状,可造成主要脏器严重损害甚至死亡的药物。如生川乌、生草乌、马钱子、巴豆、红粉(H gO) 、斑蝥等。
2.有毒类多指毒性较大、使用较大剂量后,较慢地发生中毒症状的药物。如使用不当,或用量过大,亦可造成重要脏器损害,甚至死亡。如白附子、附子、生天南星、生半夏、蟾酥、洋金花、轻粉、甘遂、芫花、常山、雄黄、木鳖子、水蛭、仙茅、白果、大戟、商陆、牵牛子、蓖麻子、蜈蚣、白花蛇、朱砂、苍耳子、全蝎、苦楝皮、硫黄、山豆根(广豆根)等。
3.小毒类多指一些毒性较小,但使用不慎或用量较大,或久用蓄积亦可使机体出现毒副作用的药物。一般不损害重要组织器官,症状较轻,不易造成死亡。如细辛、红大戟、苦杏仁、鸦胆子、急性子、蛇床子、川楝子、南鹤虱、密陀僧、重楼、猪牙皂、刺蒺藜、土鳖虫、艾叶、吴茱萸等。
198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第23号令,关于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,毒性药品管理品种中,毒性中药品种如下。
砒石(红砒、白砒)、砒霜、水银、生马钱子、生川乌、生草乌、生白附子、生附子、生半夏、生南星、生巴豆、斑蝥、青娘虫、红娘虫、生甘遂、生狼毒、生藤黄、生千金子、生天仙子、闹羊花、雪上一枝蒿、红升丹、白降丹、蟾酥、洋金花、红粉、轻粉、雄黄。
国家卫生部2002年51号文“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”中将以下59种中药材列入禁用物品,名单如下(按笔画顺序排列)。
八角莲、八里麻、千金子、土青木香、山莨菪、川乌、广防己、马桑叶、马钱子、六角莲、天仙子、巴豆、水银、长春花、甘遂、生天南星、生半夏、生白附子、生狼毒、白降丹、石蒜、关木通、农吉利、夹竹桃、朱砂、米壳(罂粟壳)、红升丹、红豆杉、红茴香、红粉、羊角拗、羊踯躅、丽江山慈菇、京大戟、昆明山海棠、河豚、闹羊花、青娘虫、鱼藤、洋地黄、洋金花、牵牛子、砒石(白砒、红砒、砒霜)、草乌、香加皮(杠柳皮)、骆驼蓬、鬼臼、莽草、铁棒槌、铃兰、雪上一枝蒿、黄花夹竹桃、斑蝥、硫黄、雄黄、雷公藤、颠茄、藜芦、蟾酥。第2章 急性中毒的诊断为了及时有效地抢救中毒病人,使他们尽快转危为安,恢复健康,首先必须正确诊断。正确诊断的依据来源于详细询问病史、全面体格检查、正确的实验室数据及仔细的现场观察和对毒物的及早、准确的分析等。
一、了解中毒史
应由中毒者自己或陪同者叙述。医师应问明所用何药,包括药物的形态、颜色、气味、来源、使用剂量、时间、途径及原先健康情况等,属急性中毒还是慢性中毒;了解初期发病症状,有否中毒治疗史,用过何种解毒药,并要求将剩余毒物送来检验(或毒物标本包装)及提供现场情况;了解近期思想情绪,以防病人有意伪造病史。在做详细了解并记录在案的同时,应警惕病情的变化,特别是对昏迷不醒者,防止漏诊或误诊。
二、体格检查
对危重的中药中毒病人,为争取抢救时间,首先观察其典型症状和体征,如曼陀罗类(阿托品类)中毒,瞳孔散大、颜面潮红、口干·舌燥、心搏加快等。乌头类中毒则知觉麻木、言语困难、血压下降、心律失常等。阿片类(吗啡类)中毒则呼吸抑制、瞳孔缩小等。番木鳖中毒则呈现全身性强直性惊厥等。抓住这些典型症状,结合其他检查,往往可以争取时间,有效地施行抢救。但有些中毒是没有特异性症状的,且典型症状的出现往往是中毒较重或晚期,因此,要做出诊断,必须做进一步的重点检查,并随时复查病情、与家属交流、结合现场观察、进行毒物分析等。
重点检查以下几点:①皮肤、口唇颜色及损伤情况;②瞳孔大小、对光反应,结膜有无充血;③体表温度、湿度及皮肤弹性;④病人的神志状态:清醒、昏迷或谵妄;⑤肌肉有无抽搐及痉挛;⑥呼吸的速率、节律幅度,呼气有无特殊气味,肺部有无啰音;⑦心搏的次数、节律及血压;⑧腹部有无压痛;⑨呕吐物及排泄物有无特殊气味及颜色;①检查衣服上有无药渍。对轻症患者,则需全面检查,如血液中有关酶类检查等,以做出正确诊断。
三、实验室检查
对中毒者做一般常规化验,如有必要需做肝肾功能、基础代谢、心电图检查等。针对可疑毒物,采集大小便、呕吐物、胃洗出液、血液等标本,在抢救的同时,及早做定性或定量检查。有毒的植物、动物或矿物药,可采集同样的标本,请有关单位鉴定。
救治时间的早晚、是否进行分秒必争的抢救是抢救成功与否及预后效果如何的关键。通过对中毒史的询问及体格检查,大体可以确定是否中毒及中毒种类与程度,配合实验室的鉴定工作,积极进行抢救。急性中毒者的症状有轻重之分,一般早期出现消化道症状,如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,以及呼吸频率、心率的改变,甚至出现休克、昏迷、烦躁、惊厥、麻痹等。




